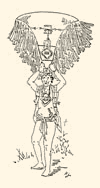賽夏族的矮靈祭是全族性的祭儀活動(圖1、2、3、4),通常在小米收穫之後,稻米已熟但尚未收穫前之間舉行,並每隔一年舉行一次。矮靈祭團分南北二部,南祭團被視為該祭儀之正宗,比北祭團早一日舉行儀式。南北祭團以下則包含若干亞祭團,其成員與上述祖靈祭祭團相一致。欲舉行矮靈祭之時,南北兩祭團的長老們各代表己團會同約定祭期;約定祭期的次日,兩祭團長老各在自己祭團內會商,指定本屆司祭。南祭團由固定的氏族擁有司祭的地位,在北祭團則由朱姓各家輪流擔任;其下之各亞祭團主祭,則南北二部均為輪值制。矮靈的信仰和儀式顯示出台灣島上族群間極動態的關係。儀式不僅做為與超自然間溝通的手段,更呈現出其如何與其他制度結合、維護社會運作的順暢,保持不穩定的社會關係的功能。 類似於泰雅族,賽夏族也有將屬於同一大河流域各社,聯合組成一個攻守同盟稱為意謂「一張弓」或「一條溪」組織的團體。在此團體中,擁立一個共同領袖,並有一個同盟首長會議;會議之內容大體限於戰爭、祭儀與土地使用的權益問題。此類組織大體屬臨時性的;在平時,處理同一攻守同盟內之矮靈祭與敵首祭事宜,對外則成為攻守同盟的單位。原有的主要共同流域部落同盟包括上坪流域的 Sai-kirapa、大東河流域的Sai-waro、小東河流域的 Sai-raiin,以及紙湖溪流域的 Sai-shawe等支系。較為接近的幾個共同流域,又聯合為南(Sai-maghahybon)、北(Sai-kirapa)二個共同戰鬥聯盟;其劃分界線就是現在南、北兩群的分界。人類學家鄭依憶的研究顯示,目前南、北地群的區分觀念越加明顯,除了地域上距離的原因之外,二群分別組成祭團、舉行矮人祭典,強化了主觀意識上的差異,應該也是主要影響因素之一。 在賽夏人的社會文化運作中,我們可以體會權威制度與親屬原則結合的重要性。一個氏族在部落中不但形成一個主要的共同行動單位,各主要氏族更分別扮演宗教活動角色,聯合形成一個有類似各種會社(associations)的社會。每一氏族有其個別的權威基礎,獲得權威者可以取得其世襲的地位。年齡與在系譜中的地位,開始成為形成個人權威的重要依據;權威的逐漸集中化,使得以親屬結構為基礎的社會基本單位,在社會中扮演一個以宗教儀式團體為整合社會的重要因素,並因此而漸漸呈現出階層化的一些性質。 與其他的原住民族群一樣,賽夏族的族群關係自古即相當複雜。許多「傳統」物質文化要素的表現上,顯然是和鄰近的泰雅族部落強烈的相互接觸、影響的結果,比方說服飾、織布紋樣、黥面、獵首儀式等都是。人類學家胡家瑜的研究便指出,雖然賽夏人與平埔的道卡斯族的文化習俗、物質表現也有部分相似之處,卻不及泰雅族的影響。除了早期南島語系民族的交互作用之外,近期漢人文化,尤其是客家族群的大量移民此區,也對賽夏族造成很大的影響。不但食、衣、住、行的方式受到影響,如:吃雞酒、醃菜、住屋加堂號,宗教信仰方面如「伯公」(土地公)、祖宗牌位、神龕的使用等也很快地被接受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