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圖1.文面老人 |
 圖2.文面老人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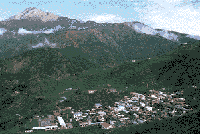 圖3.力行部落(仁愛鄉) |
 圖4.力行部落(仁愛鄉) |
 圖5.新建家屋、穀倉、結婚台。 |
 圖6.祭典歌舞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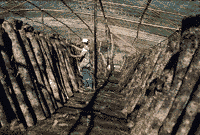 圖7.香菇種植(紅香) |
|
台灣民族誌 高山生活、信仰與社會規範 文/王嵩山 ‧圖/趙啟明 目前擁有八萬餘人口的泰雅族典型的高山居民(圖1、2),集中型的居住聚落(圖3、4)平均高度僅次於布農族,疆域是所有台灣原住民中最大的,涵蓋台北、花蓮、新竹、南投、台中等縣的山區。聚落往往因耕地不足、人口增加而不斷分化。 誠如社會學家M. Mauss所指出的,由道德意識所構成的神聖存在,足以成為思考與行動的基礎,宗教信仰與社會生活(圖5、6)的道德規範,在泰雅人的日常生活中佔據重要的地位。泰雅族被認為沒有發展出嚴整的親屬組織,可以說除了家庭以外,不存在較大範圍的具體親屬群體;其親屬組織主要是以個人為中心的雙系團體。例如,李亦園院士的研究指出:南澳群泰雅人的高山生活非常著重於超自然處境的適應,忽略單系親族群的組織原則,親族群團結力極為鬆懈;而他們的偏重雙系原則又不能構成有效的群體,以作為他們適應環境的組織,因此泰雅人轉而借重於另一種組織原則的群體——嘎嘎(gaga 或 gaya),藉以發揮社會群體的功能。「嘎嘎」具有下列幾個主要特徵。 首先,「嘎嘎」是以超自然觀念與信仰而非親族關係為基礎的團體。「嘎嘎」的成員即使以若干近親家族為中心,實際上卻常包括若干完全無親族關係的家庭;原則上,「嘎嘎」成員是可以自由參加和退出的。其次,「嘎嘎」是一個以「祖靈」(rutuh)之信仰為中心,組成「遵守共同祖訓、共同擁有超自然集體知識」的儀式團體。屬於同一個「嘎嘎」的人共同舉行重要祭儀,共同遵守超自然力量rutuh的訓示,服膺一切應該遵守的禁忌。第三,「嘎嘎」亦是一個共同生產團體,「嘎嘎」的組織在農業經濟功能上具有重要的意義;在特定的時間內,同「嘎嘎」的人共同參加狩獵,共同遵守主要榖物的種植規則;因此,「嘎嘎」是一個共勞互助團體;同「嘎嘎」的人在開墾、播種、除草、收割、築屋及其他特殊事件時互相幫忙。最後,「嘎嘎」更可視為一個共同的行為規範團體;泰雅人相信〝rutuh〞是宇宙的主宰,也是一切人生禍福的根源。泰雅人虔敬服從〝rutuh〞,不但無條件的遵守其訓示,有時還供奉犧牲,以求赦罪;泰雅人也相信某個人犯禁,同「嘎嘎」的人都蒙受其害;由於同「嘎嘎」的人都互相負有規範行為的職責,不幸有人犯禁,則須殺豬分食於「嘎嘎」成員,作為對他們的賠償。 因此,「嘎嘎」團體同時具備了宗教、地域、單系親屬群的社會功能;這個共同遵守「祖訓」的儀式團體,代替一般單系親族群,發揮規範行為、促進共勞合作、同負罪責的功能。而這種包含同地域群、廣義的同祖群或同祖居地群的共祭、共守禁忌的團體,由於其成員並不能通過系譜來證明其同祖關係,而且成員時常可以加入或退出的組成原則,而使泰雅社會中權力不斷累積的可能性減弱。 每一個泰雅聚落的形成,都以共同儀式「嘎嘎」團體為基礎;一個老部落可因人口的增多,分裂為包括有數個「嘎嘎」的部落。一個新的聚落不能沒有「嘎嘎」組織。泰雅人相信,只有聚集同「嘎嘎」團的人共同活動才能獲得生活的保障;所以在分出新部落時必須是集合同「嘎嘎」的人前往,不能單獨一家家地找尋耕地。不只如此,當一個「嘎嘎」團的靈力消失,或多人想要前往新地開墾,可以向別的「嘎嘎」團「購買」其「嘎嘎」。李亦園先生認為這種情況表現出泰雅人「農業技術的一種秘密傳承」。正因為如此,泰雅部落居民接近資源的平等機會便因此種「可轉換的技術之傳承」而得以穩固下來。 上述情形呈現出「嘎嘎」的雙重特徵。首先,「嘎嘎」是社會上具有道德與信仰意義的組織,而且此種道德與信仰更因有其經濟或農業技術(圖7)上的支持而更形加強;其次,「嘎嘎」又指涉維持社會秩序的支配性價值或規範。這種情形也清楚的見之於其政治體系中的領袖性質之上。 南澳群泰雅人認為一個部落的定義是:「對外是一個外交獨立的單位,藉著參加同流域聚落同盟的機會,以維持與他聚落間均勢態勢;對內則必須內務獨立,不受他聚落之干擾,並保護同聚落中人之安全」。每聚落通常設頭目一人,是全聚落對外交涉的全權代表,也是對內所有「嘎嘎」團體之間的調停者。雖然如此,一個聚落首長並沒有任何的特權,甚至他也不能干預其他「嘎嘎」團體的內務。因此,在聚落中實際握有習慣法執行權的,乃是每個「嘎嘎」的領袖。 一般來說,作為聚落領袖者通常是某個「嘎嘎」團體的領袖。聚落內主要的政治社會活動,如聚落與「嘎嘎」之間,或「嘎嘎」與「嘎嘎」之間,都藉著聚落頭目、「嘎嘎」領袖、由各個「嘎嘎」所組成的聯合會議、聚落大會、「嘎嘎」大會等之內在聯繫而成的交錯關係予以固定,並使各個「點」之間得以保持平衡狀態。聚落裡「嘎嘎」領袖、長老會議、「嘎嘎」會議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交錯的;在「嘎嘎」中真正能決定各種事務的,則為「嘎嘎」會議。至於聚落外部,泰雅人經常基於共同集體安全的需要,形成一個「同流域的同盟」,對外採聯合的軍事行動,同盟聚落之間則以和平共存為基本態度。這個超聚落的組織,以同盟的「首長會議」為決定或解決共同事務的機關。 泰雅社會的權威主要基於信仰而非通過宗教組織而形成,權威普化存在於整個社會上。由於個人的能力,也就是其後天累積的各種豐富經驗,而被選為領導者的「嘎嘎」團體領袖是宗教儀式的執行者,也就是司祭。其主要的責任是:推算農事曆期,主持祭禮,同時引導進行各項工作。「嘎嘎」領袖是遵守〝rutuh〞各種遺訓的表率,獲得來自〝rutuh〞及其所繁衍出來的「嘎嘎」之庇祐。正如傾向於平權的社會,泰雅領導者的政治權威以「非集中化」為其組成原則,領導權靠個人的後天能力來獲得,主要的決策機構是可以平等表達意見的會議;所有政治組織,都採取有事才成立,一旦事情解決則隨之解散的形態。而其領導權的性質,更顯示出政治權威之基於個人的能力(耕種、打獵),以及〝rutuh〞的庇祐之基礎。換言之,泰雅社會整合與衝突運作的基礎,在於〝rutuh〞的支配性文化價值與分合極易具動態性質的「嘎嘎」組織原則之上。 上述社會文化性質也影響了泰雅人對資本主義的適應。比方說,人類學家陳茂泰以南投縣仁愛鄉的道澤、卡母界泰雅社群,由山田燒墾方式適應到果園經營為例指出:泰雅人藉由原有的「嘎嘎」轉換而來的教會組織解決資金、運銷等問題。但是,當其適應當前經濟環境而發展出的組織,隨著經濟體系的性質而不斷擴大,藉以維持其經濟效益時,這種類型的團體卻因缺乏足夠的組織能力,而導致這些團體因不能有效運作而漸趨於沒落。 |
 圖1.文面老人 |
 圖2.文面老人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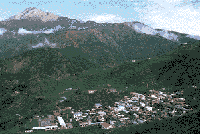 圖3.力行部落(仁愛鄉) |
 圖4.力行部落(仁愛鄉) |
 圖5.新建家屋、穀倉、結婚台。 |
 圖6.祭典歌舞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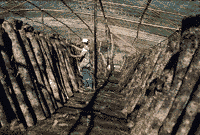 圖7.香菇種植(紅香) |